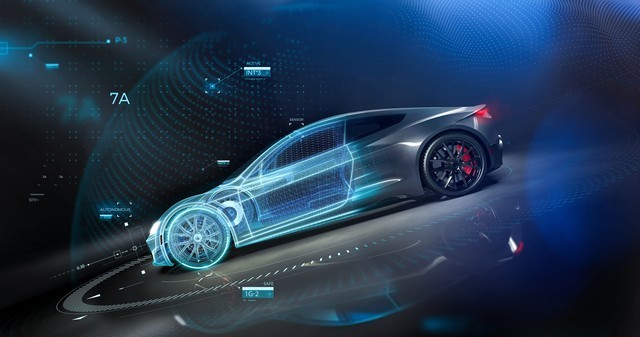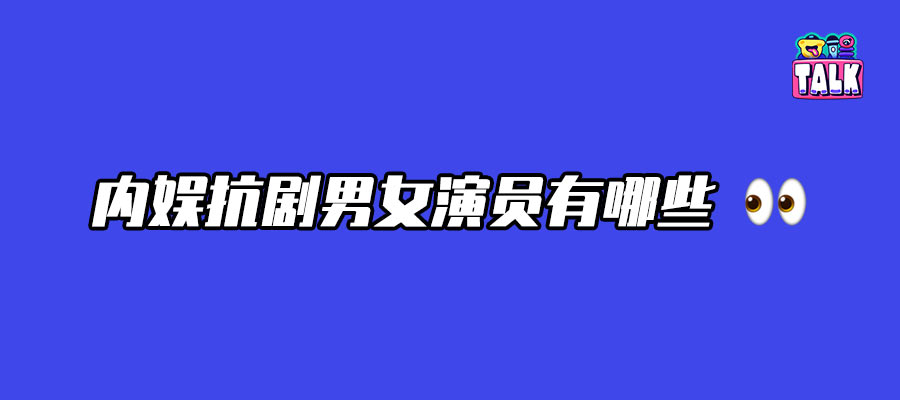H&M于9月9日在上海淮海中路651号重开中国最大旗舰店“House of H&M”,门店面积近3000平方米,涵盖女装、男装、童装及首次引入的H&M Home家居系列,并融合咖啡、花店、展览与直播空间。该位置曾为H&M2007年进入中国市场时的首店所在地,2022年因业绩与舆论压力关闭。
财报数据显示,H&M在华门店数从2019年的500余家缩减至2023年的约300家,北京三里屯和淮海路等核心商圈门店相继退出。过去一年,品牌通过关闭低效门店、升级南京东路、北京悦荟广场等核心点位,并在深圳开设新店进行策略调整。此次回归被视为H&M通过旗舰化重塑市场存在感的关键举措。
今年以来,ZARA、UR、优衣库等品牌亦加速推进旗舰店战略,集中资源打造“少而大”的门店形态。ZARA在南京新街口开设2500㎡旗舰店,内设咖啡区与“Fit Check”影棚;UR在伦敦设立两层沉浸式空间;优衣库落地成都城市旗舰店,引入循环回收与定制服务;太平鸟在淮海路推出集合多品牌与艺术展陈的“超体店”。
运动品牌同步跟进,lululemon对三里屯门店重装升级为千平级旗舰店,On昂跑在太古里开设双层旗舰店并配备互动科技装置,迪桑特将旗舰店设于高尔夫会所,绑定赛事资源与高端圈层。本土品牌方面,森马新开奥莱旗舰店,雅戈尔持续布局服饰体验馆。
此类大店不仅扩展物理面积,更强化功能复合性。H&M旗舰店集成家居、餐饮、展览与内容生产;优衣库通过RFID与自助结账提升库存效率;ZARA标准化社交媒体素材拍摄流程;On利用互动设备传播产品技术信息,实现线上话题转化。数字化成为大店运营的核心支撑,推动门店向线上线下联动中枢转型。
选址集中于一二线城市核心商圈,包括上海淮海路、南京新街口、北京三里屯、成都太古里及伦敦Westfield等地段,以保障自然客流并增强品牌曝光能力。旗舰店由此兼具“品牌地标”与“传播放大器”双重属性。
ZARA母公司Inditex在2024财年财报中披露,集团门店总数下降2.3%,但经营总面积增长2.0%;H&M强调成本控制、产品组合优化、供应链效率提升及门店体验改善为利润回升主因;雅戈尔管理层表示未来或将难见街边小店。
行业共识转向以效率与标杆价值替代数量扩张。电商渗透率上升使消费者购衣需求可在线完成,线下门店需承担体验营造、氛围构建与话题制造功能。赢商大数据显示,“非标准首店”占比从2022年的34.7%升至2024年的47.1%,反映品牌由单一销售向复合生活场景转变的趋势。
供给端面临库存高企压力,促使品牌重构门店体系。相比分散小店,大店具备更强库存消化与物流承接能力,结合数字化系统可实现库存共享与跨渠道调拨,提高周转效率。优衣库RFID系统与自助结账设计旨在缩短流转周期,减少人力与资金占用,大店成为缓解供应链压力的重要出口。
品牌焕新亦是驱动因素。快时尚需借象征性门店修复形象,运动品牌强化生活方式定位,本土品牌则试图摆脱“低价大众”标签,通过艺术化、设计化叙事提升品牌形象。旗舰店被广泛视为品牌升级核心工具。
然而,大店模式亦面临多重挑战。首先,核心商圈租金、人力与运营成本高昂,若客流与转化不足,可能由“品牌地标”转为“资金黑洞”,坪效提升能否覆盖额外支出尚存疑问。其次,定制化场景难以规模化复制,当旗舰店下沉至二三线城市时,传播效应与商业回报不确定性增加。
此外,消费者对体验的新鲜感存在边际递减效应,咖啡、展览、课程等配置一旦普及,差异化优势将被削弱,品牌需持续更新内容维持吸引力。最后,在电商与社交媒体分流注意力背景下,若缺乏有效数字化联动,大店易沦为“空心地标”,无法带动线上转化或形成持续话题。
旗舰店战略折射出服饰行业在新旧零售秩序间的探索路径。它既是应对电商冲击、库存积压与品牌心智稀释的自救手段,也是一场高成本博弈。短期可制造声量、刷新形象,但长期可持续性取决于客流稳定性、成本覆盖能力、体验迭代速度及线上线下协同水平。当前,旗舰店并非确定性增长路径,而是一次关于未来零售形态的高风险实验,考验品牌在场景构建、供应链管理与数字技术应用间的综合平衡能力。
免责声明:本文内容由开放的智能模型自动生成,仅供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