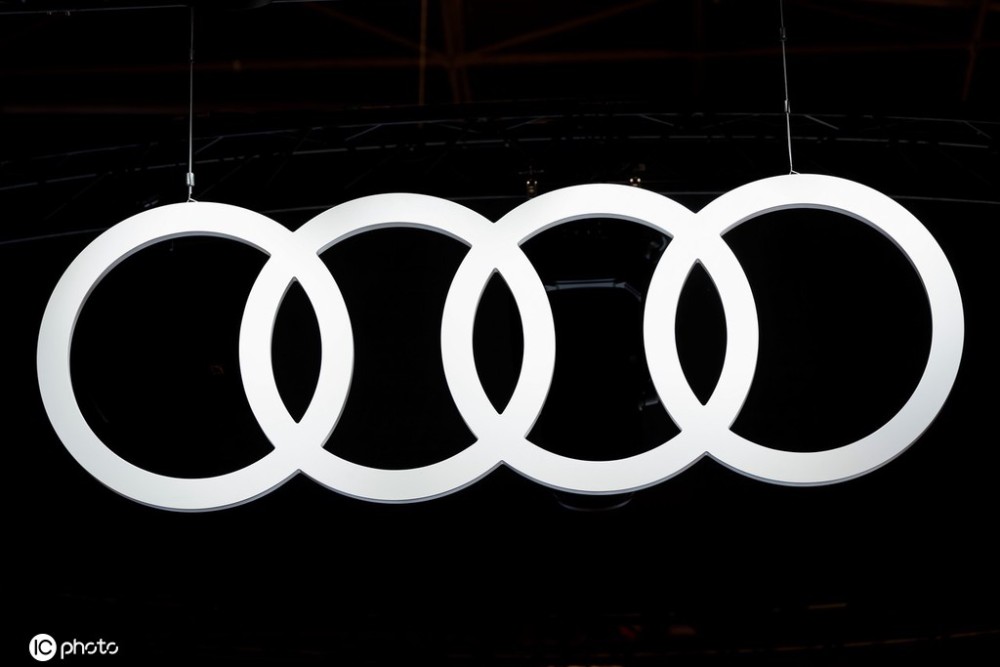根据Tubi和Harris Poll的联合报告,73%的Z世代表示对追随潮流感到疲惫。
这种厌倦不仅体现在穿衣打扮上,也反映在这一代人对消费和生活的整体态度中。
微趋势(Microtrends)指生命周期极短的审美趋势,由美国社会学家马克·J·佩恩于2007年提出。
当下流行风格更迭速度加快,媒体统计显示推荐机制下几乎每三到五周就出现新风格,部分快时尚品牌甚至一周一换。
《时尚芭莎》曾为近年热门微观趋势列出A-Z清单,显示流行风格日益零碎化。
球鞋领域亦如此,过去爆款如Nike Air Force、Air Max可长期统治市场,如今Samba或Speedcat等需依赖社交媒体维持热度。
消费者普遍不相信这些新款能在几十年后仍保持当前热度。
类似现象存在于Bape鲨鱼牙迷彩卫衣、Supreme Box Logo等经典单品之后,当前缺乏具有强烈标识性的潮流产品。
Lululemon瑜伽裤、Fog服饰、加拿大鹅羽绒服等多依赖季节或话题热度,存在明显周期性。
消费者少有“愿攒一年钱只为购买”的冲动,时尚快速迭代导致消费模式变化。
The Port Press批评快时尚品牌推出过多廉价服装,造成“买更多但穿更少”,增加衣物丢弃频率与浪费。
Newsweek 2024年调查显示,42%的Z世代为追求时尚牺牲生活必需消费,56%因此感财务压力,47%存在心理压力。
Statista《全球Z世代时尚》研究显示约30%的Z世代已刻意规避快时尚,另有约30%表示将来会这么做。
时尚秀场与红毯设计被批缺乏创新,审美趋于统一,公众人物辨识度下降。
Instagram与TikTok网红中受欢迎的白人女性外貌高度相似,呈现卡戴珊式面部特征趋同。
The Guardian指出社媒充斥“悲伤米色”家居风格,颜色审美亦趋单调。
游戏行业频繁重制旧IP,《最后生还者》PS5版、《怪物猎人荒野》《数码宝贝物语 时空异客》均为经典延续。
电影方面,《攻壳机动队》《花样年华》及宫崎骏作品重映体现对旧作眷恋。
奢侈品牌频繁致敬复古,Louis Vuitton复刻村上隆合作系列20周年款,BV重启档案款式,Jimmy Choo推出1997-2001专辑。
社媒上西部牛仔风、经济上行审美、波西米亚风等复古词条成为灵感来源。
反复复刻被视为缺乏创新,怀旧情绪加剧未来期望稀薄感。
算法、资本与用户互动加速社媒审美标准化,信息爆发反而增加无意义感。
短视频平台日均接触数百条重复内容,舞蹈、广告、梗文化易引发疲劳。
Pew Research Center 2025年研究显示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时间长但兴趣减退,正能量感知从2022年67%降至2024年52%。
48%青少年认为社交媒体对同龄人影响负面,较2022年上升16%。
WGSN 2025年报告指出39%年轻人称算法推荐难以发现真正有价值内容。
信息摄取失望促使怀旧成为替代选择。
部分年轻人对未经历的过去产生类似乡愁的情绪,表现为对二手市场的热衷。
调查数据显示超80%的18-34岁消费者会购买二手服装,较55-64岁群体高出至少30个百分点。
Vintage与古着成社媒潮人标签,Vinted与闲鱼摆脱负面形象,被视为更具性价比与趣味性的市场。
二手商品被认为价格稳定,部分具升值潜力。
Statista调查显示46%的Z世代与千禧一代购衣时考虑二手转售价值。
国内市场出现“古着=奢侈品”说法,反映价格差异显著。
复古被视为比新潮更持久且价值更高,涵盖商业与风格双重维度。
“爷爷风”中前代单品成为前沿时尚,十年前外套可能仍质量上乘。
年轻人流行“花得更少,期望更多”的消费观,复古市场被视为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渠道。
Vintage市场发展反映年轻一代关注情绪价值与社会价值,而非仅物质属性。
多项调查显示年轻人更愿为兴趣课程、手作、定制化产品支付费用。
Jellycat快闪、毛绒文创、Labubu流行体现情绪价值驱动消费。
Value-driven purchases在中国调查显示近100%的18-35岁受访者愿为情感价值买单。
日本年轻群体对Emoi(情感共鸣)元素敏感,如平成怀旧风、泪系自拍。
Impero研究发现82%的Z世代渴望融入特定社群。
福山在《身份政治》中指出身份认同是当代个体行为核心动力,归属特定社群带来认同与价值感。
IYKYK(If You Know, You Know)成为隐秘暗号,二次元“痛文化”通过谷子、棉花娃娃与装饰形成爱好者过滤网。
阶级符号亦促成共鸣,卡车司机帽、字母印花短袖、标语帆布包成表达态度方式。
环境与经济因素使社会对Z世代描述偏负面,部分反映对未来信心缺失。
IPSOS 2023年全球民调显示60%受访者希望世界变回原样。
传媒艺术家博伊姆在《怀旧的未来》中提出怀旧是对未来的投射,追寻的不仅是过去表象而是未来思考。
当前怀旧热潮体现Z世代对未来发展的期待,消费行为成为保全自我的方式。
McKinsey报告指出截至2024年秋末,欧洲五国80%至95%的Z世代与千禧一代有降级消费行为,X世代及更早世代该比例为52%至81%。
欧盟与美国整体消费者中约24.6%对经济条件持消极态度,法国34%不满当前财务状况。
普华永道概括Z世代三大消费矛盾:数字原住民却偏好实体店;品牌意识强却偏爱自有品牌;花钱谨慎但情感驱动下迅速消费。
TikTok兴起No-Spend Challenge,参与者整月除必需品外不消费。
Loud Budgeting提倡公开拒绝超预算支出,如“餐厅超出本月预算”或“正攒钱购车不出行”。
矛盾消费观显现:明知旧单品更保值,仍难拒更新趋势。
Lululemon在美国核心市场出现疲软,Crocs洞洞鞋、Stanley保温杯等热门产品同时位列最流行与最可能过时榜单。
Stanley保温杯在女性中排本季趋势第二,也在退出趋势榜第二,显示“正流行但正失宠”。
Crocs处于相同队列,反映产品热度短暂且不稳定。
Z世代因微趋势过多而感无聊疲惫,试图脱离社媒裹挟发展自我形象,又受流量影响难以抗拒。
此类情绪覆盖生活多方面,社会形容词从热血拼搏转为疲劳崩溃。
Allwork.Space数据显示74%的Z世代员工报告至少中度工作压力,成各年龄段中压力最高群体。
Z世代在亲密关系中更易情绪回避与感受高孤独感。
成长中经历经济危机、流行病、气候变化、虚假信息与社会运动多重冲击塑造其特殊性。
他们思想前卫、敢于批评,又脆弱敏感,易受网络情绪与文化符号影响。
研究发现37%的Z世代并非真正热爱流行单品,购物仅为缓解压力。
“跟风”本身成为压力源,时尚追求演变为负面情绪推动的恶性循环。
对Z世代而言,追求酷实则是渴望在世界中拥有话语权与归属感的表现。
免责声明:本文内容由开放的智能模型自动生成,仅供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