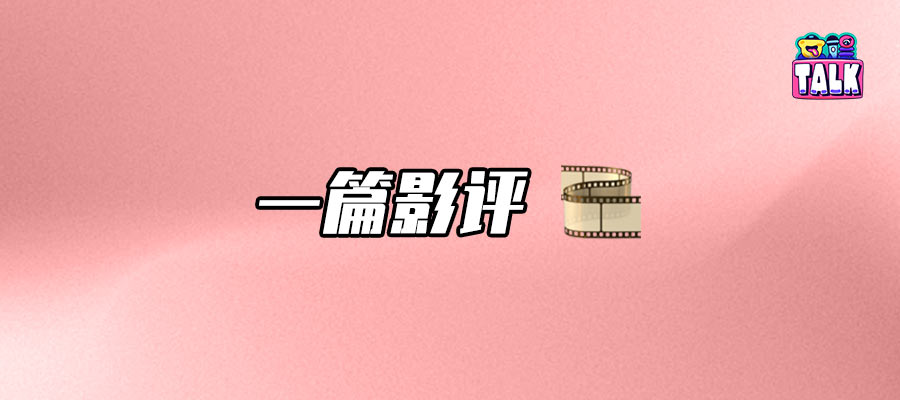
作者 / 安 济
编辑 / 朱 婷
运营 / 狮子座
站在《恶意》北京首映礼的台上,陈思诚正面回应了他自己和影片主演之一李庚希的舆论争议。“果郡王”“资源咖”“京圈公主”——“都是扯淡!没有那么多阴谋论,没有被资本控制,我们就是一帮爱电影的,普普通通的,为电影、为自己的理想和热爱工作的努力的人。”
这番针对舆论标签的激烈反击,恰与电影《恶意》开篇的“网络审判实验”形成荒诞闭环:当两千名观众低头滑动手机,用投票键决定“嫌疑人该被淹死”时,没人意识到自己正拧紧恶意的螺丝。
此刻的路演现场,似乎成为影片主题的延伸剧场。陈思诚痛斥阴谋论的姿态,被媒体和粉丝的镜头捕捉后迅速切片传播,随后#陈思诚回应网络传闻##陈思诚说李庚希京圈公主传闻是扯淡#等话题冲上热搜。评论区的反应也很有趣,“真性情!”与“自导自演营销戏”的声浪对撞,让现实的情景竟也与影片故事对照了起来。
截至目前,《恶意》的点映及预售总票房突破2600万,刘慈欣背书“颠覆认知”的捷报刷屏时,豆瓣短评区正被“平庸”“陈思诚套路复刻”“情绪勒索”的声讨淹没。更有观众表示:“影片批判流量操控大众,自己却用营销数据绑架口碑。”恩,怎么不算是精准点破《恶意》影评割裂的根源呢。
kk也看了《恶意》,值得肯定的是,作为暑期档备受期待的影片之一,《恶意》聚焦网络暴力的题材视角在当下的电影市场是稀缺的,其表达也是大胆的。但很显然,作为编剧的陈思诚试图用“社会手术刀”的野心剖开网络暴力的脓疮,可惜片子最终还是落入“陈思诚式悬疑万能创可贴”的套路,这就导致《恶意》在题材上的锐利,直接败给叙事的惰性和逻辑bug。
今天,我们就来聊聊《恶意》的好与不好。(ps:下文涉及大量剧透~介意者勿看)
01、三个“恶女”?!
“我们拍的不是恶人,是普通人如何成为恶的零件。”
《恶意》聚焦网络暴力主题,讲述一起癌症患者与护士同时坠楼案引发的舆论风暴。张小斐饰演的记者叶攀在调查中先后将护士和母亲报道为嫌疑人,引发汹涌的网络暴力。电影开头有一个"网络审判"实验的场景,展示了网民如何被片面信息煽动。
然而这场令人脊背发凉的社会实验,早已为整部电影埋下伏笔,影院里的观众尚未意识到,自己即将成为《恶意》这场银幕中的社会实验的参与者。
影片中的第一次反转发生在抗癌天使的母亲尤茜(梅婷饰)那句撕裂心肺的“护士推我女儿坠楼”,在媒体的“剪刀”下,这句控诉变成了护士李悦的“杀人实锤”:#白衣恶魔李悦#话题下收割着阅读量话题,瞬间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。这场话题的制造者叶攀盯着飙升的点击率嘶吼:“我要看她上热搜。”真相开始在巨大的流量池里淹没。
在未经警方调查的前提下,互联网舆论场的各方仅凭李悦的“夜店”照片和“小三”传言,就把她塑造成凶手,而“道爷”的出现提供了一段ICU视频又把新的“凶手”锁定在了患者母亲尤茜身上,因为她在为女儿插呼吸机时有了几秒的犹豫,也因为她组建新家庭后再次怀孕,这位母亲就要面临“放弃大女儿、亲手杀死女儿”的舆论审判。
第三次反转也因此发生,为了转移尤茜身上的网暴风暴而再制造一个热点,这一次,叶攀站到了话题的中心,成为第三个被网暴的女性——白衣天使成为杀人凶手,抗癌母亲变成杀女凶手,正义记者成为刽子手、纯真实习生化身复仇者,《恶意》几乎呈现了一种“全员恶女”的生态,女性们在恶意传递链中轮番转换受害与施暴的双重身份。
影片通过跨媒介技术将抽象恶意转化为生理压迫体验,形成沉浸式社会实验的观影体验。
声音指导李涛表示,将2000条真实网暴评论输入AI声库,生成360度环绕的咒骂洪流;键盘敲击声从偶然单响到暴雨轰鸣(群体癫狂),暗喻个体质疑发展成群体癫狂的理性被淹没的过程;画面比例也跟随剧情从16:9缩至4:3,象征舆论场对个体认知的窄化挤压。
借此,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仿佛也被戴上了认知枷锁,成为影片中网暴的千万大众中的一员。这也正是《恶意》最亮眼的部分,聚焦网络暴力题材,将观众带入这场舆论风暴里,指向我们屡见不鲜的残酷现实:
2022年,15岁的寻亲少年刘学州因生母不实指控遭全网围猎,自媒体大V捏造其“索要天价房产”的谣言,数百万网友的谩骂如海啸般将他吞噬,最终他在三亚海滩服药自尽,遗书里“阳光照在海面,我也归于大海”的绝笔成为网络暴力最刺眼的墓志铭。
类似事件每时每刻都在发生,恶意从未消失,它只是换上新衣,在下一个热搜里等待我们入局。而电影存在的意义,就是用影像艺术把这些从未消失的丑陋显示剥开展示给大众,在批判现实的同时,引发每个观众的思考。
02、叙事与表达的失衡:高概念下的深层溃败
可惜的是,原本该是一把锋利的“社会手术刀”的《恶意》,却在悬疑类型的砧板上卷了刃。
影片机械地塞进多重反转:护士虐童→ICU视频网暴死者母亲→实习生复仇→自杀的真相→观众问责,看似环环相扣,但遗憾的是,每一次反转都并不出乎观众的意料。在当下的市场环境里,悬疑类型已经是相对成熟的存在,也长期培养了一批经验丰富、审美要求高的观众,当年被《误杀》震撼的观众,如今也很难再为“陈氏悬疑流水线”买单了。
更重要的是,从护士李悦背负污名到尤茜成为众矢之的,再到李庚希饰演的实习生突然抛出“新罪证”把叶攀送上舆论审判席,每一次的反转都靠碾碎一个女性声誉当燃料,影片的叙事也沦为提线木偶戏。
而悬疑的部分,研磨在本片后30分钟拖沓如公益广告的循环播放里,陈思诚一面高喊“探讨人性灰度”,另一边,影片里的黄轩饰演的警察制式机械地查IP、查监控,张子贤饰演的刻板资本大佬(每句台词都在念诵“黑暗森林法则”)简化矛盾,当张小斐愤怒地喊出“不把世界让给讨厌的人”时,影片预想中精心构建的现实图景免不了碎成廉价鸡汤的渣滓。
面谱化严重的角色设定暴露的是影片在文本层面的虚张声势,所以即使梅婷的眼泪救得了角色,却救不回《恶意》割裂的叙事。营销号口中张小斐的演技名场面,也改变不了影片叙事的单薄,同时,那些真正应该拷问的网暴现象、集体无意识狂欢都在孙越、吕严等喜剧人的幽默客串中消解了。
当然,对观众来说最无语的还是结局,警察偶然间发现的监控才能还尤茜一个清白,到最后才打开李悦的柜子看到跳楼少女的独白,在经历了网暴凌迟、诬陷绞杀、跳楼未遂的梅婷,只能因为死去的女儿的一段话而与一切和解,之前的剧情伏笔都被创作者抛之脑后的了,只是强行给观众塞了一张“温情赎罪券”。
当现实的伤口被糖霜覆盖,《恶意》批判的锋芒便融化成黏腻的糖浆,在这一维度上,这场原本应该酣畅淋漓的社会拷问变成了一个未完成的实验。
03、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实主义影片?
观众对现实主义影片的期待是手术刀,而非创可贴。
当《恶意》挥起聚焦网络暴力的旗子,我们期待它像《我不是药神》解剖医疗制度般,剖开“流量经济-算法豢养-法律失语”的恶性循环;当孙越饰演的无良主播消解严肃性时,我们盼望出现对流量时代媒体话语权与系统之间的讨论——现实主义的终极使命不是展示伤口,而是探查“感染源”。可惜《恶意》在即将切入肌理时,还是换上了陈思诚的“万能创可贴”。
《恶意》的拧巴恰是当下现实题材的缩影:它比2012年的电影《搜索》更完整地展示了网暴生成的链条,和后者一样回避平台责任,比2023年的影片《热搜》更震撼于技术呈现,却同样陷入情绪煽动。观众真正渴望的,永远是捅破伤口后的下个动作。
在此之前,《消失的她》证明悬疑类型能承载现实议题,但成功关键在于让反转服务于真相揭露而非遮蔽真相;《坠落的审判》正用每个扎根人性深度的选择告诉观众:高级的悬疑,是让观众在人性迷宫中迷失,而非被编剧的套路戏耍。
而《恶意》五重反转堆砌叙事快感时,观众并没有看到更创新更实验和更深刻的表达,最后好像只是留下了“多传递善意,不要传播恶意”的说教。在这一维度,《恶意》虽然填补了同类型在市场上的稀缺性,但似乎又仅此而已。
所以它也再次暴露了陈思诚的“悬疑公式”的致命伤:反转沦为KPI式的流水线生产,深刻议题便成了悬疑套件的装饰性贴膜。那些被碾碎的女性声誉、被消解的系统拷问、被糖霜包裹的残酷真相,最终让“手术刀”卷刃成钝器。
但值得肯定的是,《恶意》还是完成了它作为商业电影的文化使命:让每一个观众都思考其在舆论场中的身份,唤醒大众对善意而非恶意的渴望。我们批判它的不足,也正是因为在乎——在乎现实主义不该是类型片的镶金边骨灰盒,在乎那些被“多传递善意”的空话掩埋的真问题,也在乎一部试图探讨社会议题的悬疑类型片的完整度和优质程度。
影片里有句台词是,新闻人有底线,新闻才有底线。电影同理,电影足够精彩,观众才会真的为之鼓掌欢呼。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