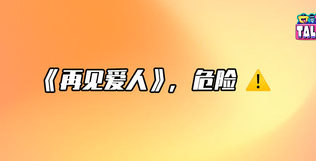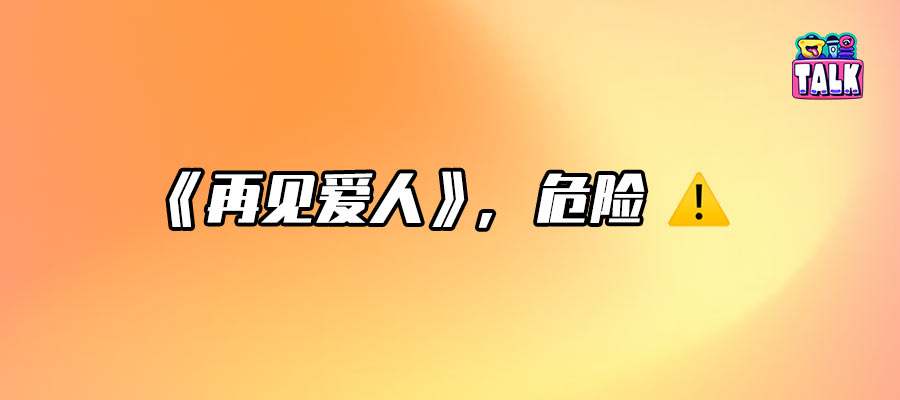
作者 / zeze
编辑 / 阿 笔
运营 / 狮子座
呃,婚姻纪实观察类真人秀,能一个人参加吗?
听起来是有些离谱,但确实发生在《再见爱人》第五季身上了。
10月23日,节目组官微发博称新一期延期上线,第二天节目是正常播出了,但嘉宾路行在经历“行贿”风波后,宣布退出节目。连夜剪掉路行的镜头后,节目时长缩短了,原本三对嘉宾变成两对半了……
这操作还是太超前(癫)了,不过放在《再见爱人》身上,好像又并不奇怪,毕竟从本季开播以来,发生在嘉宾身上的话题和“幺蛾子”就没停过,此前,何美延与梁淞的家暴争议、李施嬅与车崇健的情感纠葛,接连将节目推上舆论漩涡。热度是有了,但把嘉宾推上风口浪尖,或者说,费尽心思地选了舆论的“危险人物”上综艺,对节目组到底有啥好处啊?
社交媒体上,大众正在忙着给嘉宾“赛博诊病”,NPD、阿斯、反社会型人格等专业心理学名词成为新的攻击武器,“互联网医生”们通过剪辑片段确诊着每一个表情、每一句话语,仿佛一档情感观察节目已变身三甲医院的诊室现场。
然而谁还记得,《再见爱人》第一季开播时豆瓣高达8.9分的治愈时光,那时热搜关键词是“破防”、“泪崩”与“意难平”。章贺在悬崖边那声“感谢你”,郭柯宇含泪微笑回应,成为无数观众心中的经典画面——原来,即使爱情终结,尊重与理解依然可以存在。
观众在早年的《再见爱人》里看到的不是“疯子”“病人”的猎奇与戏剧,而是自身情感的映照。但从张婉婷开始,节目的走向逐渐偏离轨道,女性嘉宾成为众矢之的,被攻击为“NPD典型”的“疯女人”还有当时被骂惨了的麦琳。
年初,《再见爱人》的制片人、总导演刘乐还做客鲁豫的播客《岩中花述》,提到”抛弃爆品思维,做过得了自己这关的精品足矣”,而如今的《再见爱人》已经完全看不出符合精品的品相,在节目核心幕后团队没有大变动的情况下,到今年第五季,彻底从情感疗愈乌托邦滑向“精神病”的观察与呈现。
热度是逐渐走高,但治愈底色逐渐褪去,偏离了第一季的治愈性、思考力,取而代之的是标签化、病理化的全民诊断,虽然制片人多次表示节目没有剧本,但节目组本身筛选出来的都是个顶个戏剧张力拉满的“问题嘉宾”。这档曾影响无数人婚恋观的节目,正面临着彻底迷失初衷的危险。
一、早期治愈:情感共鸣与婚姻真相的温柔呈现
回忆起《再见爱人》最初的模样,温暖治愈的底色依然没有褪去。
第一季里,章贺与郭柯宇的故事让不少人第一次意识到,婚姻的终结不必是狗血的闹剧,而可以是体面的告别。两人十年婚姻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节奏里,一个早睡早起,一个夜晚活跃;一个喜欢运动,一个偏爱安静。
他们在节目中展现的,不是仇恨与抱怨,而是试图理解彼此差异的努力,虽然失败了,婚姻走向了终点,但抛开结果来看,还是可以看到他们个体的魅力和闪光点。没有脸谱化的大反派,没有狗血的剧情,只有普通人面对情感疏离时的无奈与挣扎,以及那份中国式离婚中最稀缺的品质——体面。
即使是曾因“直男癌”言论引发争议的魏巍(kk),在第二季中也展现了用东北式幽默化解矛盾的能力。他与佟晨洁关于“要孩子”的争论,呈现了婚姻中价值观碰撞的常态,而非一方对另一方的压迫。
观察室此时还处在理智在线(不诊病)的阶段,引导观众看到作为人类会有的多面性、复杂性,能理解嘉宾的想法与不安——那时的观察员,更像是观众的朋友,陪着大家一起哭、一起笑,一起思考亲密关系的复杂面貌。
再比如老王和朱雅琼,之前老王多次否定朱雅琼的创作,却能意识到和自己在一起时的她在发光,观众也看得出来他们之间存在沟通与理解问题,也看得出他们其实还是相爱,只是在感情里遇到了障碍。这种复杂性与矛盾性,恰恰是早期《再见爱人》最珍贵之处——
它拒绝简单地将人分为“好人”与“坏人”,而是呈现每个人在关系中的局限与努力。观众从中看到的不是“病态”,而是普遍存在于亲密关系中的沟通困境与情感需求。那时的节目,像一面镜子,照见我们自己在感情中的模样;像一位朋友,陪伴我们思考如何更好地爱与被爱。
然而,美好的时光转瞬即逝,随着热度攀升,节目组似乎发现了一条获取流量的“捷径”——与其呈现复杂真实的情感关系,不如放大冲突、制造对立。节目的重心,悄悄从“展现亲密关系的多样性”滑向了“搜集情感关系中的疯子”。感情的复杂性逐渐演化为抓马、制造“疯子”,节目的治愈底色开始褪去。
二、走向危险:从情感共鸣到“确诊”的转向
危险的转向从第二季开始变得明显。张婉婷与宋宁峰的出现,彻底改变了节目的讨论方向。
张婉婷带来的“窒息感”成为节目标签,她的情绪波动被观众诊断为“边缘型人格障碍”,宋宁峰的沉默则被标记为“被动攻击型人格”。社交媒体上,心理学专业术语开始成为攻击的武器,观察室的分析也越来越“临床化”,“创伤反应”、“触发机制”等术语被频繁提起,进一步强化了观众的“确诊”冲动。节目播出期间,张婉婷的话题热度居高不下,理性讨论的声音被淹没在情绪化的指责中。
到了第四季,麦琳与李行亮将这种病态推向了高点。麦琳被描述为“疯女人”被指“自私、不顾大局且缺乏同理心”,网友通过节目碎片化信息就给她贴上“npd(自恋型人格障碍)”等心理学标签进行审判。
而节目组的剪辑在其中承担了重要功能,一到麦琳出场配乐就变了,矛盾点集中释放(甚至是抢鲜版提前释放),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冲突、收割了流量。当时就有媒体批评了对麦琳的“全网围剿”是“媒体伦理的失范”是,一场“‘猎巫’狂欢”。
麦琳被骂得体无完肤,再多辩解都没用。节目播出一年后,李行亮最终发长文抗议网暴,称当时基于保密协议无法发声,但已经过了这么久,该骂的都骂完了,澄清和解释也显得那么无能为力。
“熏鸡事件”后,《再见爱人》已经彻底从情感交流平台沦为制造疯男疯女、全员病理诊断大会,人的复杂性被简化为临床症状,以此,来收获更高的热度。观众不再满足于情感共鸣,而是纷纷化身“互联网实习医生”,热衷于为嘉宾贴上各种心理学标签。
但事实上,不管是边缘型人格还是其他精神类问题的诊断,都有严格的医学标准,仅凭电视剪辑的情绪片段就下诊断,既不专业也不道德。然而,这种理性的声音在流量的狂欢中显得微弱。节目组通过蒙太奇手法,有意无意地制造了“疯子”,换来了热度,却失去了初心。
至此,这档节目已经变成了全网搜集“疯子”,然后让观众骂他们“疯”的病态极端。本季《再见爱人》的嘉宾也不例外,NPD、“原生家庭创伤”这些简化的标签,遮蔽了关系中真实存在的权力不平等、家务劳动分配和情感支持缺失等具体问题,节目组似乎演着演着就忘了,亲密关系的节目里更应该呈现和讨论的到底是什么。
三、综艺不该成为社会焦虑的放大镜
《再见爱人》从“情感治愈”到“全民确诊”的转变,反映了更深层的社会心理变化,也带来了很多致命危险。
真实感的流失与剧本感的增强首当其冲。第五季的《再见爱人》实在太像“预制菜综艺”了,一切都按模板来。三对嘉宾的故事线太过相似——邓莎和路行的“冷暴力婚姻”、何美延和梁淞的“Rapper式争吵”、李施嬅和车崇健的“八年感情终结”,都带着强烈的设计感。
共鸣的消失与猎奇的凸显成为第二个危险信号。早期节目的成功源于嘉宾婚姻状况的典型代表性。章贺与郭柯宇代表了中国式婚姻中常见的“情感失语”,魏巍与佟晨洁展现了价值观差异的调和可能,王秋雨与朱雅琼则让人看到亲密关系中肯定与否定并存的复杂面貌。
而本季的三对夫妻,却更像制作团队精心挑选的猎奇样本展览。路行比邓莎大18岁的豪门婚姻、已分手八个月的情侣复盘感情,这些设定本身就让人质疑其情感的实时性与有效性。当节目从“反映普遍情感困境”转向“展示特殊情感病例”,它已经背离了初衷。
最危险的或许是观众从观察者到审判者的角色异化。早期观众在节目中看到自己的影子,如今却扮演着道德法官与诊断医生的双重角色,不仅不负责任,还可能对嘉宾造成二次伤害。更令人担忧的是,这种“诊断文化”正从节目延伸到现实生活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心理学标签来定义伴侣和朋友,却忽略了人性的复杂与多变。
节目从展现“人人都有缺点,但都在努力”的温情叙事,变成了“正常人与疯子”的二元对立,这些的背后,很难不怀疑节目组的蒙太奇技法到底想把大众的关注点指向何处,这或许是比婚姻危机更值得警惕的社会心理危机。
当治愈让位于诊断,共情让位于审判,《再见爱人》还能否回归初心?节目究竟想透过内容呈现怎样的一个价值观——是成为用户照见自我反思的镜子,还是审判他人的武器?是理解复杂性的智慧,还是简单归类的快感?或许节目组真的该好好想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