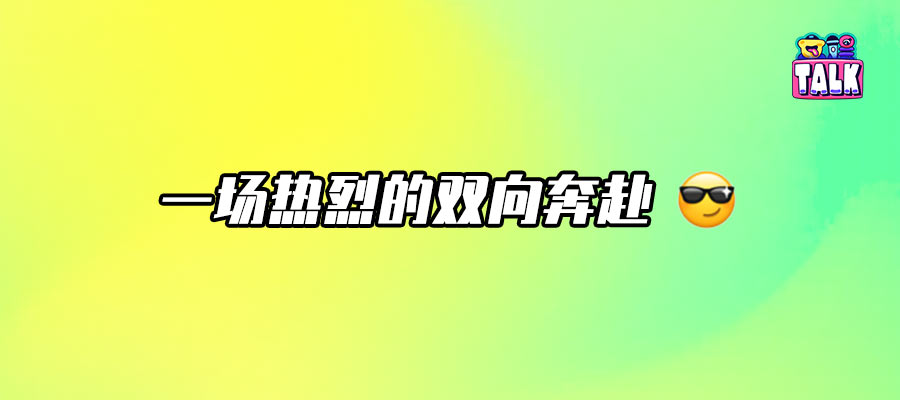10月8日,深圳地铁2号线上,一位曾在澳大利亚、美国工作,现居香港从事IT行业的印度旅客引发关于印度人全球流动的观察。今年以来,在中国多个城市出现的印度人增多现象引起关注,小红书相关帖子反映这一趋势。2020年因疫情暂停的中印直航客运服务于今年4月恢复,双方简化签证程序以改善来华旅游可达性。中国驻印度使领馆数据显示,截至2025年4月9日已核发赴华签证超8.5万件;印度靛蓝航空将于10月26日开通加尔各答—广州每日直飞航线,东航将于11月9日恢复上海浦东—德里航线,每周3班。
国务院自10月1日起实施“K字签证”新政策,印度媒体将其解读为抗衡美国H-1B签证的举措,《为何中国K字签证是对特朗普H-1B签证战的回应》等报道广泛传播,“中国K签条件”“巴基斯坦人申请中国K签”成热搜词条。与此同时,美印关系出现裂痕,《外交事务》杂志刊文指出特朗普政府自8月27日起对印度商品加征25%额外关税,使总税率升至50%,以惩罚印度大量进口俄罗斯石油;9月19日,特朗普签署公告将企业为H-1B签证申请人支付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否则不得入境。美国每年发放的H-1B签证中,印度人占比超70%,此举迫使大量印度IT从业者调整海外目的地。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未来五年将与印度实现50万人交流目标,其中5万为理工背景技术人才。
印度拥有14.6亿人口,GDP增长率超6%,经济总量达2.3万亿美元,接近英国水平,被普遍视为具有“下一个中国”潜力。《新镀金时代》认为印度将在21世纪中叶可能超过美国并挑战中国地位,形成中美印三国博弈格局。然而,印度对外资长期持谨慎态度,2020年以“国家安全”为由多轮封禁包括TikTok、WeChat、UC浏览器在内的超200个中国应用程序。一面是印度劳工完成肉身全球化,另一面则是国内市场对外资抗拒开放。
2024年印度接收海外汇款1250亿美元,居全球首位,高于墨西哥、菲律宾和中国。资金来自中东建筑工地、硅谷写字楼、伦敦医院及新加坡餐馆等地,支撑南部小城镇家庭开支与教育支出。世界银行与印度外交部数据显示,全球约有3200万至3400万印度人生活在海外,其中约1800万为“非居住印度人”(NRI),1500万余人为“印度裔公民”(PIO),使其成为海外人口最多国家。八成以上印度人支持全球化,服务业占GDP比重达55%,以外包为主的程序员贡献全国9% GDP,并占据全球55%市场份额。
项飙在《全球“猎身”,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》中将此模式称为“猎身”,即以IT劳动力作为交易品的全球流动体系。印度为生产基地,提供灵活廉价且技能不断提升的IT工人,并协调其全球流动;美国为首选目的地,吸收高质量现成人才。1992年美国设立H-1B签证制度,1998年统计显示持该签证计算机行业人员中74%为印度人,因而获称“印度人签证”。社会文化中能否成为海外IT员工影响婚姻嫁娶,成功者可带来高额嫁妆,1998-2000年间IT公司股份常作嫁妆。
特朗普提高H-1B签证成本导致“美国梦”受阻,印度IT人才需寻找新出路,服务业供需结构面临再分配。除IT从业者外,约半数海外印度裔在中东海湾地区从事建筑、运输、家政、清洁等蓝领工作。阿联酋有350万印度人,占当地人口三分之一;沙特250万;科威特与卡塔尔各超百万。印度服务业既支撑欧美IT产业,也是中东蓝领主力。经合组织数据显示,印度输出受过高等教育移民达312万,占全球65%,掌管苹果、Microsoft、谷歌等科技巨头。
印度政府尝试突破产业结构单一问题,在IT之外探索实体产业发展。苹果公司在印度年销售额于2025财年达近90亿美元,同比增长13%。库克战略推动印度成为生产基地,2025财年印度制造iPhone产量同比增长近60%;2025年4月至7月出口额达75亿美元。苹果首次在印度生产所有全新机型,并向玻璃后盖、金属外壳、电池模组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,供应商网络扩至45家以上。
2014年莫迪政府提出“Make in India”计划,目标2030年制造业占GDP比重从15%提升至25%。十年间推行PLI(生产链接激励)计划吸引约190亿美元投资,带动手机、电子、制药、汽车零部件等行业扩张。2025财年苹果在印度生产额达220亿美元,出口量增长近六成,约80% iPhone由印度出口。印度通信部长称本土销售手机99.2%为本地制造。全球供应链重构背景下,印度成为“China + 1”战略重要落点,但存在质控危机:部分组装厂合格率仅约50%,高端部件仍依赖中国、越南进口,现实更接近“半成品工业”。
印度制造业面临四大限制:一是产业链配套薄弱,尤其半导体、精密模具、核心电子元件缺失,增加制造成本;二是基础设施不足,物流效率低于中国与东南亚,电力不稳、港口拥堵、地区政策不一制约企业发展;三是劳动力结构失衡,每年新增超1200万劳动力,具备工业技能者不足30%,低附加值服务业吸纳主要就业;四是政策与行政效率低下,外资抱怨审批周期长、税制复杂、关税波动大,苹果亦需游说设备税法,制度摩擦削弱“Make in India”执行力。
尽管制造业产出增长、投资扩大、出口上升,但占GDP比重十年间始终徘徊于15%至16%,未能实现结构性转型。项飙指出海外印度工人虽在全球市场立足,但仍坚守“家庭至上”与“虔诚奉教”的印度文化认同。外企招聘中普遍存在“只有印度人才能管理印度人”认知,因员工频繁跳槽、短期内要求升职加薪,中介倾向通过印度人开办的劳力行招募。
观察印度市场14年的Tata指出,印度社会上下层间存在强烈支配与掌控思维。某印度甲方对外籍沟通温和,对本地员工则粗暴刻薄,双方均视之为常态。这种等级观念与财富高度集中密切相关。国际基金组织报告称印度为亚洲主要经济体中贫富差距最大国,身家超10亿美元富豪超百人,仅次于美中俄。2017年富豪财富总额达4790亿美元,百万美元富豪达17.8万人。瑞士信贷报告显示最富1%掌握全国超40%财富,底层40%收入总和不及前者十分之一。经济增长成果被少数人掌控,形成强大政商网络。
超级富豪依靠土地、自然资源、政府合同与许可证积累财富,与权力紧密绑定,被称为“宝莱坞寡头”。《新镀金时代》用“镀金时代”形容其外表光鲜内里腐朽的政治经济环境。风险投资人贾扬特·辛哈与政治学家阿舒托什·瓦尔什尼呼吁限制超级富豪权利,指“经济活力是腐朽而疯狂的”。富豪阶层恐惧外资打破垄断格局,保护主义成为维护财富集中与政治稳定的防御机制。
近年来印度税务部门对壳牌、诺基亚、IBM、沃尔玛、凯恩能源等外资企业展开调查并开高额罚单,日韩企业亦遭遇类似情况,印度因此被称为“跨国企业坟场”。跨境电商从业者表示印度自恃为新增长极,不再急于欢迎外企。印度文化中惯于采取压价、中间商赚差价、强制技术转让、争夺供应链话语权等方式争取利益,被视为商界生存之道。
民族众多导致印度未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建国。英国殖民前次大陆由数百邦国、王朝、部落组成,无统一国家概念。“印度”源自波斯语“Hindustan”,原为地理称谓。独立后尼赫鲁推行计划经济与许可证制度(License Raj),强调自立精神。1991年外汇危机促市场化改革,但采取“谨慎开放”策略:IT、制药、汽车等领域开放,农业、零售、电信设壁垒。22种官方语言、数百民族宗教群体造成区域发展不平衡,中央政策常被地方重新定义。开放在德里为改革,在比哈尔、奥迪沙等贫困邦被视为威胁,保护主义兼具经济选择与维系国家统一功能。
印度平均年龄不足30岁,全球最年轻人口结构之一,每年新增1200万劳动力。女性占人口半数但劳动参与率仅三成左右,限制发展潜力。至今被封禁的超200个中国应用程序仍未恢复运行。恒河既是印度教徒信仰中洗净罪孽、灵魂解脱之地,也是污染最严重河流之一,体现文明内在矛盾。世界的未来被认为只能存在于文明的印度。
免责声明:本文内容由开放的智能模型自动生成,仅供参考。